
施蛰存 心理小说新文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
书刊介绍
施蛰存 心理小说新文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 内容简介
短篇小说集。本书为我社"新文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改版之一种。以施蛰存小说的心理性为角度进行编选,选入其很很好的几篇短篇作品,包括《周夫人》《石秀》《梅雨之夕》等8篇心理小说。施蛰存的心理小说,指的是具有弗洛伊德色彩的心理分析小说。除了内容上的变化外,作品的表现形式也采取了诸如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等的新手法,但是并没有接近变成复刻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而是糅合了传统的中国小说的方式,做到了"中西合璧"。
%施蛰存 心理小说新文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 目录
序 吴立昌周夫人 1
鸠摩罗什 12
石秀 48
梅雨之夕 99
夜叉 115
狮子座流星 133
春阳 148
黄心大师 160%
施蛰存 心理小说新文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 节选
早在1933年,施蛰存就声言,给他冠以“新感觉主义”的头衔,“是不十分确实的”,他说,“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灯下集•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施蛰存的心理小说,应特指具有弗洛伊德色彩的心理分析小说,它与一般着重分析人物心理的小说不能等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创建于19世纪末,是在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上均与传统心理学迥异的一个心理学流派。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性压抑、释梦等理论,自20世纪20年代陆续被引入我国文坛之后,对鲁迅、郭沫若、杨振声、许杰、沈从文等众多作家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运用其观点和方法比较自觉、比较严格,创作比较集中,成果也比较丰硕的,则是施蛰存。因此,给他冠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小说家”的头衔才是“十分确实的”。
当施蛰存以感怀往昔的情绪,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正式的**个短篇集《上元灯》于1929年出版并获得好评时,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同上)此时,一方面,施蛰存读了许多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仅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关于“现代派”一席谈》)显尼志勒描写维也纳上流社会享乐生活时,往往强调性本能的作用,并重视刻画人物隐秘的性心理,因而颇受弗洛伊德赞赏,后者甚至引用他的某些小说做理论根据;弗洛伊德还发觉显尼志勒通过感觉或细致的观察了解到的东西,正是自己在实验过程中所发现的。所以,施蛰存肯定显尼志勒小说性心理分析的特色,认为“可以与他的同乡茀罗乙特媲美”。在此期间,除了弗洛伊德、显尼志勒,施蛰存还广泛接触了与心理分析学说密切有关的霭理斯、劳伦斯的著作。另一方面,20年代末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勃兴之时,施蛰存也曾试着通过创作跟上时代大潮,但由于思想和生活环境的拘囿,他“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我只能写我的”。这样,就更加坚定了他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创作心理分析小说的决心。
《上元灯》虽然抒情的、感伤的气氛浓郁,但从总体看,还是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施蛰存的创新当然是想从现实主义之外另辟蹊径,可是他又不肯完全舍弃现实主义方法,其意图是,“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同上)从1932年后接连出版的三本创新小说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来看,施蛰存的创新确实脱胎于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的优劣恰同他的心理分析小说的成败相一致。
施蛰存的创新,首先表现为观念的变化。弗洛伊德学说的出发点是强调性本能、无意识在人的一生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施蛰存也因此确认,“性爱对于人生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薄命的戴丽莎•译者序》)从这一观念出发去选择题材(现实的或历史的)、开掘主题,自然会使作品蒙上弗洛伊德色彩。为了适应新的观念内容,在形式上也势必采取诸如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但他又不照单全收,写完全意义上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因此,不用说收在《上元灯》里的初露心理分析端倪的《周夫人》和后期留有弗洛伊德影子的《黄心大师》,就是“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的那三本集子,在人物描写、情节安排、结构布局以及语言运用方面,也仍然同传统的表现方法有着密切联系。正是这种同现实主义传统若即若离的关系,形成了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自己的特色。
在大多是性爱题材的心理分析小说里,由于施蛰存非常重视对人物无意识性心理的挖掘,就大大有助于从深层次揭示人物性格丰富复杂的内涵。弗洛伊德带着“泛性”的有色眼镜看待客观世界,将什么都与性欲挂上钩,并由此得出人性本恶的结论,当然是荒谬的。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理性的存在,相反,他倒是希望用理性压抑本能冲动,用意识控制无意识。既然“人心的所有罪恶都作为一种倾向而包含在无意识之中”a,那么,能否将本能欲望和恶念有效地用理性予以克制和压抑,就构成了人的心理活动历程,成为人的性格丰富性复杂性的根源。我们不能因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而小觑“性”在人生中的重要意义。性欲,是人的本能欲望,但在社会中如何求得满足,必定要与异性对象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发生联系;而且人还要进行有意识活动,除了生理要求外,两性之间还要发生思想感情的交流,这又牵涉到经济、政治、文化、道德、伦理等更复杂的社会内容。因此,两性关系不只是一种自然关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人的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往往就在“灵”的欲望要满足,“肉”的欲望也要满足。但事实上二者不可兼得,终而发生激烈冲突之中显现出来。《鸠摩罗什》正是这样一篇表现“灵”“肉”激烈冲突、人性战胜神性的佳作。从心理分析角度看,它淋漓尽致地揭开了隐藏于主人公德行背后的无意识性心理,从社会学批评看,高僧鸠摩罗什在性欲面前的*终败北,正是人性终于冲破道德藩篱和佛门清规,向着封建禁欲主义奏出的一曲凯歌。
从写《鸠摩罗什》开始,就产生了一个能否以心理分析观点和方法去处理表现历史题材的问题。首先要明确,历史题材的小说,是创作,不是历史。施蛰存笔下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有的征引史实较多,如《鸠摩罗什》;有的仅借古书中片言只语,敷衍成篇,如《黄心大师》,有的材料来源本身就是古人的创作,如《石秀》。我们不能以史传文学的标准去衡量它们。作者对题材的选择、剪裁,甚至想象虚构,“一切都仅仅是为了写小说,从来没有人在小说里寻求信史的!”(《施蛰存散文选集•一个永久的歉疚》)因此,根本不存在这些小说是否应该忠实于历史,是否将古人现代化的问题。郁达夫当年读了《将军底头》后曾经说过,“历史小说的优点,就在可以以自己的思想,移植到古代的人的脑里去”b。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接着的问题是,小说所描写的主人公的灵肉冲突、无意识心理等等,是否只有今人才有,古人绝无?应该肯定弗洛伊德学说除了谬误,也有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他全力探寻和研究的无意识、代表理智和审慎的“自我”对性本能冲动的压抑,就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既然如此,作家当然可以吸取弗洛伊德学说中符合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表现古代人的心理;《石秀》在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
“性”在封建时代从来被视作邪恶不净之事,所以古代小说中的英雄多被写成对“性”无动于衷,甚至根本没有性欲;淫荡的只是女人。《水浒》中的梁山好汉,除了矮脚虎王英,几乎个个如此,这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禁欲思想和歧视妇女的观念,而且在艺术表现上,势必将人物的心灵简单化,尽管在其他方面很有性格,也只是属于仅仅为某个原则(如“忠”、“义”)而存在的“扁平人物”。石秀为杨雄出谋划策残杀潘巧云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不管《水浒》把石秀写成怎样一个守礼教讲义气的英雄豪杰,他对潘巧云的态度及举动,特别是*后撺掇杨雄将潘巧云开膛剖肚的血腥场面,给读者的印象,绝不是可亲可敬,而是可怕可憎。连金圣叹都已觉察出石秀只是为了表白自己,是一个越出人之常情的一等狠毒人。周作人更看出《水浒》惨杀犯奸女子,“特别细致残忍,或有点欣赏的意思”c。所谓“欣赏”,不只指作者,也包括像石秀这样的杀手。这是一种以虐待及至残杀异性以实现欲望满足的淫虐狂变态心理。施蛰存正是将石秀诱杀潘巧云的深层动机归咎于此,从而给石秀的所行所为寻到了符合心理发展逻辑的解释。弗洛伊德说:“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可以引起神经病。实际上由于这种缺乏的结果,性的需要乃不得不使性的激动寻求变态的发泄。”d施蛰存不仅细致描写了石秀在江湖义气、封建礼教和情欲之间的内心冲突,而且深入揭示出人物怎样因“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而走向变态的性心理流程,难怪郁达夫会从施蛰存对石秀“变态地感到性欲满足”的描写中,“感到了意外的喜悦”e。施蛰存写的石秀是一个活人,不是断绝情缘的礼教观念化身。作为梁山好汉、年轻雄强的武士的石秀,当然应该以道德和义气压抑本能冲动,但不等于说在美艳的潘巧云性的诱惑面前内心不泛起些微波澜,即使在封建道德森严的宋代也是正常的。施蛰存笔下的石秀,应该说更丰富复杂,更具有人味。
因性引起的种种心理现象,既有其自然的生理基础,又与当事人所处社会现实环境密切有关,因此文学作品刻画人物性心理不能游离于社会现实,否则就会为写性而写性,只注视人的生物性,甚至会沦为色情描写。施蛰存在处理现实题材时,*值得称道的就是能异常清晰展示人物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性心理流程。《春阳》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和心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将人物性心理的萌发、跃动同周围环境的变化发展紧紧相扣,同时又从弗洛伊德性压抑说角度,在人物的举手投足间,揭示其无意识动机。女主人公婵阿姨被春阳下的南京路繁华景象激起的情欲之火,仅仅在白日梦中燃烧了一下,一当现实的因素—对巨额财富的依恋以及周围舆论、族人讥笑,使她的自我意识恢复过来,白日梦立即轻烟似的消失。本能欲望*终还是敌不过为金钱利欲和道德观念所浸透的社会关系的控制,婵阿姨内心的这场情欲波澜很快平息下去,继续一如既往,在那受压抑的独身禁欲的寂寞境遇里打发日子。婵阿姨的这段短暂的心灵波澜,既是一个小小的心理悲剧,也是个小小的社会悲剧。从婵阿姨形象的塑造,至少可以表明,只要不把人物从社会环境游离出来,那么,运用心理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雕镂人物的灵魂,特别是揭示无意识性心理,同样具有真实性,甚至比传统方法更见深度。
《狮子座流星》中的主人公卓佩珊夫人,和《春阳》里的婵阿姨一样,都是施蛰存当年“所看见的典型”。《善女人行品•序》作者不仅点明了她的生儿子的强烈愿望,而且突出她对丈夫粗鲁、肥胖、不讲礼貌、不会体贴的不满情绪,从而暗示她在性生活中受到了压抑。于是被压抑的欲望与日间生活经验—巡捕关于梦见扫帚星会生孩子的戏言、早晨的阳光、梳子落地声,十分巧妙地连缀成*后的梦,从而使主人公的无意识欲望在梦中实现。这样的描写,既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又反映了这一社会阶层妇女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急切求子的心态。
《梅雨之夕》所刻画的性心理,虽然没有直接同什么重要社会生活发生联系,但是主人公由于对妻子的隐隐不满,希求从更年轻美丽的异性身上获得补偿的无意识心理,仍然来自现实,来自主人公那特定的生活环境,仍然是社会某种人际关系的产物。作者以委婉曲折、体贴入微的笔致,烛照主人公这类知识分子隐秘的内心世界,这不也是一种灵魂的写实吗?
施蛰存回顾当年写作心理分析小说时的一个原则是,对于外来形式,只要有助于表现人物,加强主题,就可拿来为我所用,但又不能单纯追求,而应“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关于“现代派”一席谈》)这个原则在多数作品中得到了贯彻。施蛰存深知,不管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既然写的是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就不可能完全置传统方法于不顾,也不能完全脱离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相反,应尽可能将外来形式融于传统表现方法之中,以*终达到“摆脱影响”,亦即“中国化”的境界。“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优秀作家,大多是开始取法于西方,后来逐渐摆脱西方的影响,显现出本民族的特点。施蛰存当年努力探索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弗洛伊德在临床治疗中发明自由联想法,是为了让病人克服抗拒而把隐藏的无意识欲望说出。施蛰存既然要在小说中揭示人物的无意识心理,通过对人物自由联想状态的描写,显示其意识流动的轨迹,那么采用类似西方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也是势所必然。不过,它们与西方意识流小说又不尽相同,虽有人物的自由联想、意识跳动,但是作者并未退出小说,而且往往采用近似传统小说分析心理的写法,从作者的视角,通过对人物神态、动作的刻画而显示其内心,正如莫泊桑所赞赏的,“客观的作家不啰唆地解释一个人物的精神状态,而要寻求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的环境里使得这个人必定完成的行为和举止。”f至于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遵循的也是时间空间变化发展的正常秩序,所以读起来,十分清晰晓畅,不会产生像读西方意识流小说那种煞费周详的晦涩感。不仅《梅雨之夕》《春阳》等篇是这样,即使是烟火味较淡,完全描写病态心理的《魔道》《夜叉》等篇也是这样。
“一个人只有到了自我不能处理里比多的时候,才会患神经病。”g《夜叉》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神经病患者。贯穿小说始终的不是曲折复杂的情节,而是主人公的病态心理,是他那飘忽不定的意识流动。自从他瞥见船上一个白衣妖媚女人并“确然曾有过一点狎亵的思想”之后,即产生一连串的错觉和幻觉,读古书,看古画,水中芦花,屋顶炊烟,草间野兔,都与那白衣女人,与夜叉化为美女的传说联系起来,终而酿成一出在错觉中掐死无辜农家哑女的惨剧。主人公一系列错幻感觉都源于潜在的无意识欲望,亦即那“一点狎亵的思想”,再加上夜叉的传说,眼前的景象,编织成一个完整的颇能自圆其说的白日梦。作品不仅真实地表现了主人公因感知障碍而产生病态心理的全过程,而且构思精巧,描写生动,在朦胧神秘的氛围里,照样能给读者十分明晰、一气呵成之感。施蛰存在小说发表于著名刊物《东方杂志》并重读一遍后,之所以“勇气顿生”,以为“能够从绝路中挣扎出生路来”恐怕就在于他对外来形式这种有节制的采用。至于后期的《黄心大师》,则更是有意识地“用近乎宋人词话的文体”,吸收了中国旧小说的优点,行云流水般地委婉诉说了女主人公由于长期性压抑所造成的悲凉一生。然而,从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影影绰绰见到弗洛伊德的影子在晃动。与《鸠摩罗什》《石秀》等篇相比,此篇可看作是观念上还保留心理分析的合理因子,形式上更加中国化民族化的可喜尝试。
为什么施蛰存写出《夜叉》之后“勇气顿生”,但实际上还是没有“能够从绝路中挣扎出生路来”呢?就因为他只沉湎于形式的创新,而忽视了内容的现实主义要求。比如《魔道》,就是从“病榻上的妄想中产生出来的”。《夜叉》呢?据作者解说,是乘火车时,“偶然探首出车窗外,看见后面一节列车中,有一个女人的头伸出着,她迎着风,张着嘴,俨然像一个正在被扼死的女人,这使我忽然在种种的联想中构成了一个plot,这就是《夜叉》。”按照这样的路子下去,直到写出《凶宅》这样一个仅仅根据报纸一段老的新闻编造的描写淫虐狂杀人狂的刺激感官的荒诞故事,才恍然大悟:“从《魔道》写到《凶宅》,实在是已经写到魔道里去了”,“我已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硬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弗洛伊德对人的本质的看法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他完全忽视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决定意义,纯粹从生物学角度去理解。如果认识不到弗洛伊德学说这个根本缺陷,创作时很可能远离现实,仅从生理病理学角度去一味刻画人物的变态、怪异心理,那就肯定要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30年代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从而失去广大读者。施蛰存能够及时总结教训,及时从“绝路”改弦易辙,回归到现实主义轨道,是非常明智的。后期的短篇集《小珍集》以及《黄心大师》就是这一明智抉择的成果。
施蛰存的心理小说,像一颗流星,在30年代文坛上空一划而过,这固然有作家自身的原因,但是,与当年文坛对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的片面理解也不无关系。从施蛰存成功的心理小说可以看出,作者的笔不仅拓宽了人物的心灵领域,而且渗透到无意识底层。作者在刻画人物的梦幻、变态心理的同时,又没有忽视将人物行为的心理动因置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去表现,因此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有浮在心灵高层的清醒意识,而且有潜入心灵深谷的无意识流动。心理活动的多层次、多侧面必然加强了人物性格的立体感,从而达到用传统描写方法不易达到的艺术效果。由此可见,只要正视现实,不脱离现实,作家完全可以大胆运用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写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好作品。当时的一些批评,指出施蛰存某些作品脱离现实的缺点是应该的,但对施蛰存创新的正面经验却肯定不够,甚至大大忽视了,因而就不可能从积极方面给创新者以鼓励和支持。30年代特定的历史环境给了现实主义文学驰骋文苑的大好时机,但在此同时,有些左翼作家往往把现实主义当作一个自我封闭的固定模式,并以此去要求所有作家的创作,这样当然就谈不上用开放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当时正在西方兴起的包括心理分析在内的新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像鲁迅那样敢于融古今中外于一炉,将现代主义中国化的气势恢弘的文学大师也就难以再现了。
以施蛰存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小说,只是30年代文坛来去匆匆的过客,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始终未成气候,以致弄得50年后,竟然还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当成时髦玩意着实热了一阵子,现在想想,实在令人遗憾得很呵。
施蛰存 心理小说新文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 作者简介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字蛰存,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等 ,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编者吴立昌,江苏镇江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开设“文学概论”、“写作”、“沈从文研究”、“精神分析与文学”、“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论争专题”、“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等本科生、研究生课程。
施蛰存 心理小说新文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 本书特色
吴立昌编的《施蛰存心理小说》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是“新文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的之一。施蛰存的小说,宛如身着华丽的中式旗袍,在传统民乐的伴奏下跳着异国的华尔兹。施蛰存胸襟豪放超然,不耽于党同伐异的文坛纷争。本作品的表现形式采取了诸如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等的新手法,但是并没有完全变成复刻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而是糅合了传统的中国小说的方式,做到了”中西合璧”。
施蛰存 心理小说新文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 目录
序 吴立昌周夫人 1
鸠摩罗什 12
石秀 48
梅雨之夕 99
夜叉 115
狮子座流星 133
春阳 148
黄心大师 160
施蛰存 心理小说新文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 节选
早在1933年,施蛰存就声言,给他冠以“新感觉主义”的头衔,“是不十分确实的”,他说,“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灯下集•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施蛰存的心理小说,应特指具有弗洛伊德色彩的心理分析小说,它与一般着重分析人物心理的小说不能等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创建于19世纪末,是在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上均与传统心理学迥异的一个心理学流派。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性压抑、释梦等理论,自20世纪20年代陆续被引入我国文坛之后,对鲁迅、郭沫若、杨振声、许杰、沈从文等众多作家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运用其观点和方法比较自觉、比较严格,创作比较集中,成果也比较丰硕的,则是施蛰存。因此,给他冠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小说家”的头衔才是“十分确实的”。
当施蛰存以感怀往昔的情绪,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正式的**个短篇集《上元灯》于1929年出版并获得好评时,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同上)此时,一方面,施蛰存读了许多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仅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关于“现代派”一席谈》)显尼志勒描写维也纳上流社会享乐生活时,往往强调性本能的作用,并重视刻画人物隐秘的性心理,因而颇受弗洛伊德赞赏,后者甚至引用他的某些小说做理论根据;弗洛伊德还发觉显尼志勒通过感觉或细致的观察了解到的东西,正是自己在实验过程中所发现的。所以,施蛰存肯定显尼志勒小说性心理分析的特色,认为“可以与他的同乡茀罗乙特媲美”。在此期间,除了弗洛伊德、显尼志勒,施蛰存还广泛接触了与心理分析学说密切有关的霭理斯、劳伦斯的著作。另一方面,20年代末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勃兴之时,施蛰存也曾试着通过创作跟上时代大潮,但由于思想和生活环境的拘囿,他“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我只能写我的”。这样,就更加坚定了他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创作心理分析小说的决心。
《上元灯》虽然抒情的、感伤的气氛浓郁,但从总体看,还是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施蛰存的创新当然是想从现实主义之外另辟蹊径,可是他又不肯完全舍弃现实主义方法,其意图是,“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同上)从1932年后接连出版的三本创新小说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来看,施蛰存的创新确实脱胎于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的优劣恰同他的心理分析小说的成败相一致。
施蛰存的创新,首先表现为观念的变化。弗洛伊德学说的出发点是强调性本能、无意识在人的一生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施蛰存也因此确认,“性爱对于人生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薄命的戴丽莎•译者序》)从这一观念出发去选择题材(现实的或历史的)、开掘主题,自然会使作品蒙上弗洛伊德色彩。为了适应新的观念内容,在形式上也势必采取诸如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但他又不照单全收,写完全意义上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因此,不用说收在《上元灯》里的初露心理分析端倪的《周夫人》和后期留有弗洛伊德影子的《黄心大师》,就是“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的那三本集子,在人物描写、情节安排、结构布局以及语言运用方面,也仍然同传统的表现方法有着密切联系。正是这种同现实主义传统若即若离的关系,形成了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自己的特色。
在大多是性爱题材的心理分析小说里,由于施蛰存非常重视对人物无意识性心理的挖掘,就大大有助于从深层次揭示人物性格丰富复杂的内涵。弗洛伊德带着“泛性”的有色眼镜看待客观世界,将什么都与性欲挂上钩,并由此得出人性本恶的结论,当然是荒谬的。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理性的存在,相反,他倒是希望用理性压抑本能冲动,用意识控制无意识。既然“人心的所有罪恶都作为一种倾向而包含在无意识之中”a,那么,能否将本能欲望和恶念有效地用理性予以克制和压抑,就构成了人的心理活动历程,成为人的性格丰富性复杂性的根源。我们不能因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而小觑“性”在人生中的重要意义。性欲,是人的本能欲望,但在社会中如何求得满足,必定要与异性对象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发生联系;而且人还要进行有意识活动,除了生理要求外,两性之间还要发生思想感情的交流,这又牵涉到经济、政治、文化、道德、伦理等更复杂的社会内容。因此,两性关系不只是一种自然关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人的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往往就在“灵”的欲望要满足,“肉”的欲望也要满足。但事实上二者不可兼得,终而发生激烈冲突之中显现出来。《鸠摩罗什》正是这样一篇表现“灵”“肉”激烈冲突、人性战胜神性的佳作。从心理分析角度看,它淋漓尽致地揭开了隐藏于主人公德行背后的无意识性心理,从社会学批评看,高僧鸠摩罗什在性欲面前的*终败北,正是人性终于冲破道德藩篱和佛门清规,向着封建禁欲主义奏出的一曲凯歌。
从写《鸠摩罗什》开始,就产生了一个能否以心理分析观点和方法去处理表现历史题材的问题。首先要明确,历史题材的小说,是创作,不是历史。施蛰存笔下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有的征引史实较多,如《鸠摩罗什》;有的仅借古书中片言只语,敷衍成篇,如《黄心大师》,有的材料来源本身就是古人的创作,如《石秀》。我们不能以史传文学的标准去衡量它们。作者对题材的选择、剪裁,甚至想象虚构,“一切都仅仅是为了写小说,从来没有人在小说里寻求信史的!”(《施蛰存散文选集•一个永久的歉疚》)因此,根本不存在这些小说是否应该忠实于历史,是否将古人现代化的问题。郁达夫当年读了《将军底头》后曾经说过,“历史小说的优点,就在可以以自己的思想,移植到古代的人的脑里去”b。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接着的问题是,小说所描写的主人公的灵肉冲突、无意识心理等等,是否只有今人才有,古人绝无?应该肯定弗洛伊德学说除了谬误,也有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他全力探寻和研究的无意识、代表理智和审慎的“自我”对性本能冲动的压抑,就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既然如此,作家当然可以吸取弗洛伊德学说中符合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表现古代人的心理;《石秀》在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
“性”在封建时代从来被视作邪恶不净之事,所以古代小说中的英雄多被写成对“性”无动于衷,甚至根本没有性欲;淫荡的只是女人。《水浒》中的梁山好汉,除了矮脚虎王英,几乎个个如此,这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禁欲思想和歧视妇女的观念,而且在艺术表现上,势必将人物的心灵简单化,尽管在其他方面很有性格,也只是属于仅仅为某个原则(如“忠”、“义”)而存在的“扁平人物”。石秀为杨雄出谋划策残杀潘巧云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不管《水浒》把石秀写成怎样一个守礼教讲义气的英雄豪杰,他对潘巧云的态度及举动,特别是*后撺掇杨雄将潘巧云开膛剖肚的血腥场面,给读者的印象,绝不是可亲可敬,而是可怕可憎。连金圣叹都已觉察出石秀只是为了表白自己,是一个越出人之常情的一等狠毒人。周作人更看出《水浒》惨杀犯奸女子,“特别细致残忍,或有点欣赏的意思”c。所谓“欣赏”,不只指作者,也包括像石秀这样的杀手。这是一种以虐待及至残杀异性以实现欲望满足的淫虐狂变态心理。施蛰存正是将石秀诱杀潘巧云的深层动机归咎于此,从而给石秀的所行所为寻到了符合心理发展逻辑的解释。弗洛伊德说:“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可以引起神经病。实际上由于这种缺乏的结果,性的需要乃不得不使性的激动寻求变态的发泄。”d施蛰存不仅细致描写了石秀在江湖义气、封建礼教和情欲之间的内心冲突,而且深入揭示出人物怎样因“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而走向变态的性心理流程,难怪郁达夫会从施蛰存对石秀“变态地感到性欲满足”的描写中,“感到了意外的喜悦”e。施蛰存写的石秀是一个活人,不是断绝情缘的礼教观念化身。作为梁山好汉、年轻雄强的武士的石秀,当然应该以道德和义气压抑本能冲动,但不等于说在美艳的潘巧云性的诱惑面前内心不泛起些微波澜,即使在封建道德森严的宋代也是正常的。施蛰存笔下的石秀,应该说更丰富复杂,更具有人味。
因性引起的种种心理现象,既有其自然的生理基础,又与当事人所处社会现实环境密切有关,因此文学作品刻画人物性心理不能游离于社会现实,否则就会为写性而写性,只注视人的生物性,甚至会沦为色情描写。施蛰存在处理现实题材时,*值得称道的就是能异常清晰展示人物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性心理流程。《春阳》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和心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将人物性心理的萌发、跃动同周围环境的变化发展紧紧相扣,同时又从弗洛伊德性压抑说角度,在人物的举手投足间,揭示其无意识动机。女主人公婵阿姨被春阳下的南京路繁华景象激起的情欲之火,仅仅在白日梦中燃烧了一下,一当现实的因素—对巨额财富的依恋以及周围舆论、族人讥笑,使她的自我意识恢复过来,白日梦立即轻烟似的消失。本能欲望*终还是敌不过为金钱利欲和道德观念所浸透的社会关系的控制,婵阿姨内心的这场情欲波澜很快平息下去,继续一如既往,在那受压抑的独身禁欲的寂寞境遇里打发日子。婵阿姨的这段短暂的心灵波澜,既是一个小小的心理悲剧,也是个小小的社会悲剧。从婵阿姨形象的塑造,至少可以表明,只要不把人物从社会环境游离出来,那么,运用心理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雕镂人物的灵魂,特别是揭示无意识性心理,同样具有真实性,甚至比传统方法更见深度。
《狮子座流星》中的主人公卓佩珊夫人,和《春阳》里的婵阿姨一样,都是施蛰存当年“所看见的典型”。《善女人行品•序》作者不仅点明了她的生儿子的强烈愿望,而且突出她对丈夫粗鲁、肥胖、不讲礼貌、不会体贴的不满情绪,从而暗示她在性生活中受到了压抑。于是被压抑的欲望与日间生活经验—巡捕关于梦见扫帚星会生孩子的戏言、早晨的阳光、梳子落地声,十分巧妙地连缀成*后的梦,从而使主人公的无意识欲望在梦中实现。这样的描写,既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又反映了这一社会阶层妇女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急切求子的心态。
《梅雨之夕》所刻画的性心理,虽然没有直接同什么重要社会生活发生联系,但是主人公由于对妻子的隐隐不满,希求从更年轻美丽的异性身上获得补偿的无意识心理,仍然来自现实,来自主人公那特定的生活环境,仍然是社会某种人际关系的产物。作者以委婉曲折、体贴入微的笔致,烛照主人公这类知识分子隐秘的内心世界,这不也是一种灵魂的写实吗?
施蛰存回顾当年写作心理分析小说时的一个原则是,对于外来形式,只要有助于表现人物,加强主题,就可拿来为我所用,但又不能单纯追求,而应“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关于“现代派”一席谈》)这个原则在多数作品中得到了贯彻。施蛰存深知,不管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既然写的是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就不可能完全置传统方法于不顾,也不能完全脱离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相反,应尽可能将外来形式融于传统表现方法之中,以*终达到“摆脱影响”,亦即“中国化”的境界。“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优秀作家,大多是开始取法于西方,后来逐渐摆脱西方的影响,显现出本民族的特点。施蛰存当年努力探索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弗洛伊德在临床治疗中发明自由联想法,是为了让病人克服抗拒而把隐藏的无意识欲望说出。施蛰存既然要在小说中揭示人物的无意识心理,通过对人物自由联想状态的描写,显示其意识流动的轨迹,那么采用类似西方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也是势所必然。不过,它们与西方意识流小说又不尽相同,虽有人物的自由联想、意识跳动,但是作者并未退出小说,而且往往采用近似传统小说分析心理的写法,从作者的视角,通过对人物神态、动作的刻画而显示其内心,正如莫泊桑所赞赏的,“客观的作家不啰唆地解释一个人物的精神状态,而要寻求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的环境里使得这个人必定完成的行为和举止。”f至于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遵循的也是时间空间变化发展的正常秩序,所以读起来,十分清晰晓畅,不会产生像读西方意识流小说那种煞费周详的晦涩感。不仅《梅雨之夕》《春阳》等篇是这样,即使是烟火味较淡,完全描写病态心理的《魔道》《夜叉》等篇也是这样。
“一个人只有到了自我不能处理里比多的时候,才会患神经病。”g《夜叉》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神经病患者。贯穿小说始终的不是曲折复杂的情节,而是主人公的病态心理,是他那飘忽不定的意识流动。自从他瞥见船上一个白衣妖媚女人并“确然曾有过一点狎亵的思想”之后,即产生一连串的错觉和幻觉,读古书,看古画,水中芦花,屋顶炊烟,草间野兔,都与那白衣女人,与夜叉化为美女的传说联系起来,终而酿成一出在错觉中掐死无辜农家哑女的惨剧。主人公一系列错幻感觉都源于潜在的无意识欲望,亦即那“一点狎亵的思想”,再加上夜叉的传说,眼前的景象,编织成一个完整的颇能自圆其说的白日梦。作品不仅真实地表现了主人公因感知障碍而产生病态心理的全过程,而且构思精巧,描写生动,在朦胧神秘的氛围里,照样能给读者十分明晰、一气呵成之感。施蛰存在小说发表于著名刊物《东方杂志》并重读一遍后,之所以“勇气顿生”,以为“能够从绝路中挣扎出生路来”恐怕就在于他对外来形式这种有节制的采用。至于后期的《黄心大师》,则更是有意识地“用近乎宋人词话的文体”,吸收了中国旧小说的优点,行云流水般地委婉诉说了女主人公由于长期性压抑所造成的悲凉一生。然而,从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影影绰绰见到弗洛伊德的影子在晃动。与《鸠摩罗什》《石秀》等篇相比,此篇可看作是观念上还保留心理分析的合理因子,形式上更加中国化民族化的可喜尝试。
为什么施蛰存写出《夜叉》之后“勇气顿生”,但实际上还是没有“能够从绝路中挣扎出生路来”呢?就因为他只沉湎于形式的创新,而忽视了内容的现实主义要求。比如《魔道》,就是从“病榻上的妄想中产生出来的”。《夜叉》呢?据作者解说,是乘火车时,“偶然探首出车窗外,看见后面一节列车中,有一个女人的头伸出着,她迎着风,张着嘴,俨然像一个正在被扼死的女人,这使我忽然在种种的联想中构成了一个plot,这就是《夜叉》。”按照这样的路子下去,直到写出《凶宅》这样一个仅仅根据报纸一段老的新闻编造的描写淫虐狂杀人狂的刺激感官的荒诞故事,才恍然大悟:“从《魔道》写到《凶宅》,实在是已经写到魔道里去了”,“我已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硬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弗洛伊德对人的本质的看法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他完全忽视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决定意义,纯粹从生物学角度去理解。如果认识不到弗洛伊德学说这个根本缺陷,创作时很可能远离现实,仅从生理病理学角度去一味刻画人物的变态、怪异心理,那就肯定要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30年代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从而失去广大读者。施蛰存能够及时总结教训,及时从“绝路”改弦易辙,回归到现实主义轨道,是非常明智的。后期的短篇集《小珍集》以及《黄心大师》就是这一明智抉择的成果。
施蛰存的心理小说,像一颗流星,在30年代文坛上空一划而过,这固然有作家自身的原因,但是,与当年文坛对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的片面理解也不无关系。从施蛰存成功的心理小说可以看出,作者的笔不仅拓宽了人物的心灵领域,而且渗透到无意识底层。作者在刻画人物的梦幻、变态心理的同时,又没有忽视将人物行为的心理动因置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去表现,因此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有浮在心灵高层的清醒意识,而且有潜入心灵深谷的无意识流动。心理活动的多层次、多侧面必然加强了人物性格的立体感,从而达到用传统描写方法不易达到的艺术效果。由此可见,只要正视现实,不脱离现实,作家完全可以大胆运用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写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好作品。当时的一些批评,指出施蛰存某些作品脱离现实的缺点是应该的,但对施蛰存创新的正面经验却肯定不够,甚至大大忽视了,因而就不可能从积极方面给创新者以鼓励和支持。30年代特定的历史环境给了现实主义文学驰骋文苑的大好时机,但在此同时,有些左翼作家往往把现实主义当作一个自我封闭的固定模式,并以此去要求所有作家的创作,这样当然就谈不上用开放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当时正在西方兴起的包括心理分析在内的新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像鲁迅那样敢于融古今中外于一炉,将现代主义中国化的气势恢弘的文学大师也就难以再现了。
以施蛰存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小说,只是30年代文坛来去匆匆的过客,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始终未成气候,以致弄得50年后,竟然还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当成时髦玩意着实热了一阵子,现在想想,实在令人遗憾得很呵。
施蛰存 心理小说新文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 作者简介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字蛰存,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等 ,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编者吴立昌,江苏镇江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开设“文学概论”、“写作”、“沈从文研究”、“精神分析与文学”、“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论争专题”、“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等本科生、研究生课程。
相关推荐
-

细读《尼各马可伦理学》
《细读《尼各马可伦理学》》内容简介: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据传是由其子尼各马可编纂,故名),在西方学府中,历来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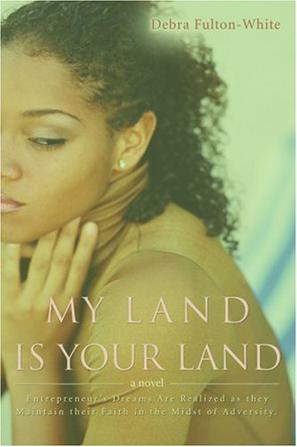
Debra FultonWhite《My Land Is Your Land》
THEPASTBackattheUniversityofBerkeley,thecommitmenttodedicatehislifetomissionaryw...
-

世俗的圣歌
《世俗的圣歌》内容简介: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是拉丁美洲文学现代化发展中影响最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不仅在拉丁美洲影响巨
-

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 本书特色《典藏:人间词话》,《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对中国古代的优秀词作进行了集中点评,是王国维在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洗...
-

青山依旧-报人读史札记三集
青山依旧-报人读史札记三集 本书特色 田东江,河北三河人,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成长于京郊潮白河畔。1978年初中毕业,读技工学校铸造专业;1985年自富拉尔基...
-

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
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 本书特色 《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是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的文章,作者原来大...
-

潜行乌贼
潜行乌贼 内容简介 作者戏称书中所收都是“东涂西抹的豆腐干”。这些长短不一的文章集新闻报道与文化时评于一体,读来还有滋有味。也许它们是色彩漂亮的蔬菜拼盘,怡人爽...
-

世界500强企业发展丛书:时间机器--施乐帕克与计算机时代的黎明
世界500强企业发展丛书:时间机器--施乐帕克与计算机时代的黎明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包括:乐队指挥、麦克劳干的蠢事、“波特大道”旁的房子、乌托邦、伯克利的第二系...
-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研究(精)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研究(精)》内容简介: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是20世纪中国学界最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被誉为《文心雕
-

白岩松-行走在爱与恨之间
白岩松-行走在爱与恨之间 本书特色 本书是一本白岩松行走、思考的散文随笔,由白岩松亲笔写序修订,是他近年来行走的所见、所感、所悟。白岩松以其一贯的冷静视角,平实...
-

文学与图像
陈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东方文学插图本史料集成及其研究”主持人。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专著《殊方异药...
-

献上一片安宁
献上一片安宁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的内容有:我认识了人民公安员、无边的仇恨、人民警察张国富、赴汤蹈火——记消防民警刘洪全同志等。献上一片安宁 目录 我认识了人民公...
-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著名考古学家。
-

善良在左.邪恶在右
善良在左.邪恶在右 本书特色本书是俄罗斯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的随笔与书信精选集。本书甄选契诃夫*有价值的书信,既有契诃夫与巨擘托尔斯泰、高尔基、柴可夫斯基、蒲宁等...
-

你不知道的美国留学
《你不知道的美国留学》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大量有来源有出处的数据,翔实客观、严谨细致地介绍了美国留学的全过程。包括前期准备、
-

远行
远行 本书特色 两年森林中的冒险猎奇之旅,一场肉体与灵魂的视觉盛宴!*特立独行、逍遥自由的梭罗,用绝美文字和浪漫深情给尘世浇一捧清凉的湖水!远行 内容简介 18...
-

战争中的飞行员
战争中的飞行员 本书特色 以一次特殊的自杀式的飞行任务展开叙述了作者在二战期间琐碎的回忆。主人公在黑夜中期待黎明,在炮火交织中陷入绝望又重新向往生机,*终在璀璨...
-

发现花未眠
《发现花未眠》内容简介:读一篇优美的散文,如品一杯茗茶,馨香绕怀,久久不忘。读一本好书,如与伟人对话,智慧之光映射身心……
-

刘东自选集
刘东自选集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的内容有:回到轴心时代、不通家法、形式合理只是必要条件和*低标准、西方的丑学、叔本华:没有意志的意志哲学家等。刘东自选集 目录 自...
-

爱你就像爱生命
爱你就像爱生命 本书特色 【情思二十年,王小波*全书信集】★李银河独家授权八卷本“王小波传世经典”★收入王小波先生*受推崇、*具收藏价值小说、随笔、书信二百余万...





